报道转载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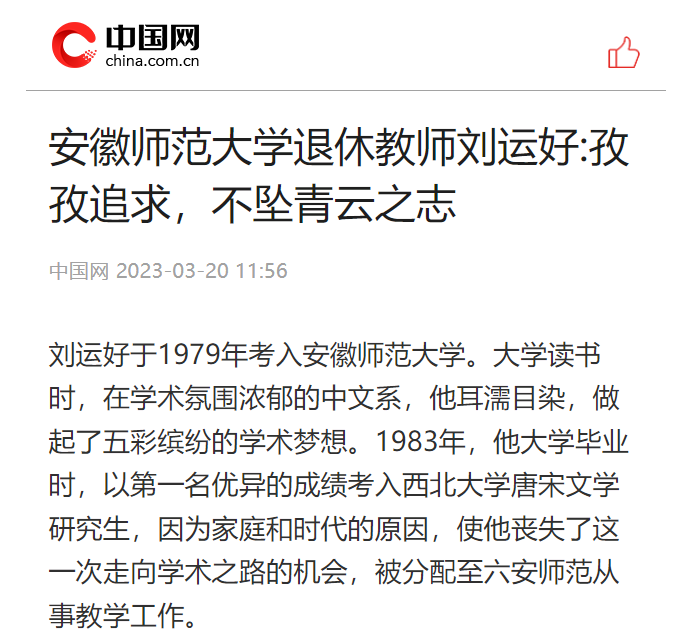
刘运好于1979年考入安徽师范大学。大学读书时,在学术氛围浓郁的中文系,他耳濡目染,做起了五彩缤纷的学术梦想。1983年,他大学毕业时,以第一名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北大学唐宋文学研究生,因为家庭和时代的原因,使他丧失了这一次走向学术之路的机会,被分配至六安师范从事教学工作。
刘运好因为他曾经有过以考上西北大学研究生的“辉煌经历”,所以在当时教育还比较落后的六安已经算是一个“人才”了,于是成为这些新兴的“高校”争相聘请的对象。然而,究竟选择上教授哪一门专业课,却不是他自己所能选择的。他们缺哪一科的专业老师,就请他顶上。为了家庭的生计,他也只能硬着头皮顶上去。那时,他在六安师专夜大学、安徽省教育学院六安教学点的中文专业分别讲授过中国古代文学史(包括作品选),在六安电视大学讲授过中国古代文化史、古代汉语,在六安联大讲授过现代汉语、写作教程。
刘运好在六安师范工作了十三周年。从前,他曾因荒废了美好的学术时光而懊恼不已,现在冷静想来也未必完全如此。除了教学相长以外,还有两件事影响了他后来的学术研究。第一件事是,他刚毕业的那几年全国勃然兴起一阵“美学—方法论”热,省教育厅师范处下拨给六安师范一大批新翻译的西方美学著作,师范老师很少关注这些新著,而我却如获至宝,一摞一摞地抱回家中,一本一本地翻阅,虽然也难免有囫囵吞枣之处,但是也时时有自己的读书心得。每有读书心得的地方,他都随时记录下来,日积月累,竟然写成一本《文学鉴赏与批评论》(初稿)。第二件事是,1993年前后,安徽大学一位语言研究所的老师邀请他参加《中华典故大辞典》编撰,本来也只是一位“学术打工仔”,但是也有两点对他后来的学术之路产生了影响。一是在做辞典的语词卡片时,他阅读了大量冷僻的清人笔记小说,这是他读书期间从未接触过的新的文献,后来他读鲁迅著作时,发现鲁迅特别注意笔记小说隐含的学术信息,杂文中有许多论断,就是以笔记小说为史料依据的。所以,他再读书时也开始注意笔记小说的史料价值。二是因为他做“学术打工”的态度认真,主编就将他“升格”为编委。编委的基本任务就是审查别人所制语词卡片的文字准确性和语典意义的概括准确性。他所审查的卡片涉及《诗经》《楚辞》《东观汉记》《后汉书》《晋书》,他趁机通读了这几种书目,其中《东观汉记》是他第一次接触,虽然篇幅不大,由于是汉代人记录汉代史,其史料意义的可靠则又在《后汉书》《汉纪》之上。现在《东观汉记》已经出版了校注本,但是对于其独特的史料意义似乎还是重视不够。他在阅读此书时,当时主要是从典故生成的时间考察,发现了大量《辞源》《唐诗大辞典》等辞书中出典《后汉书》的词条,其实在《东观汉记》中已经完备,而《东观汉记》比《后汉书》早了二百多年,于是就写了一篇文章《白璧微瑕——〈辞源〉求源中的一个失误》(《辞书研究》1995年第5期)。谁承想,这篇文章在考博时还给他增加不少分呢,这当然是后话。后来,他又参与了安徽大学这位先生主编《二十五史智慧大全》的编撰,他主要搜罗《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的资料,又再次重读此书。因为这次他被“升格”为副主编,又审读了大量书稿,自然又有新的发现,写了一篇《<智囊>与<智囊补>之比较》,后来以他爱人的名义发表在《徐州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上。

刘运好在参与上述两部书的编撰时,有留下的遗憾,也有意外的收获。留下的遗憾是,他在参与编撰《中华典故大辞典》的制作卡片过程中,发现一本清人笔记关于“莺莺塔”回声的详细记载,还发现了《辞源》出典另外一些错误,可惜因为那时他根本没有学术经验,没有随时记录下来,时过境迁,忘记了具体的书名,本来可以写出很好的学术文章,就这样活生生地丢掉了,这恐怕还不止是遗憾,简直有点教训惨痛了。意外的收获是,在编撰上述两部书时,主编请贾文昭先生审稿,他认识了贾文昭先生。先生对他所写的词条谬赞有加,并且说,你水平这么好,怎么不去考研究生呢?他就将他的家庭情况详细地告诉了先生,并且告诉他这一切困难即将过去,他的最小侄儿也已经考取中专,一毕业他就“雨过天晴”了。先生说,既然你最小侄儿已经上了中专,你现在就可以考虑考研究生,并且鼓励刘运好报考他的研究生。生活艰辛已经消磨了他曾经学术理想,他再也没有泛起过考研的念头,先生“一语惊醒梦中人”,考研的梦陡然升腾了起来。贾先生可能早已忘记了他,但是贾先生的话却深刻影响了他的一生。
因为贾文昭先生的提醒和勉励,刘运好已经决计考研了。大学读书时,他对唐宋文学最感兴趣,所做的一摞一摞读书笔记,大多数都与唐宋文学有关。于是他希望报考余恕诚先生的研究生。从方可畏老师家出来后,他直奔余老师家。余老师对他报考唐宋文学研究生非常支持,当时就打电话给学校研究生招生办。他不知是谁接电话的,只知道在余老师详细介绍了他的情况之后,余老师的脸色突然沉了下来,喃喃地说:“怎么会这样呢?”放下电话后,余老师告诉他,研究生招办说他的年龄太大了,不能报考统招研究生,只能读在职的。他顿时懵了——读在职对他有什么意义呢?师范学校也不是一个做学术的地方呀。他不知道怎么从余老师家走出来的,老师说的鼓励的话也仅仅在他耳边飘过。他漫无目的在校园里晃悠,竟然走到了他原来读书的教学大楼下面。他们离校时,楼下的玉兰花还是青葱小树,陡然间已是那样粗壮,绿荫浓密,昂扬向上,他不禁走近前去,轻轻地拍一拍那粗壮的玉兰树,深深感慨:“树犹如此,人何以堪!”那一刹那间,他的眼泪一直眼眶中打转。考研梦碎一地,刘运好又回到了生活的原点。
当时,一位同学借调在省教育厅工作,刘运好立刻找到他的联系电话,详细地咨询了同等学力报考的相关要求,确认了这一消息的可靠性。那时,他就像打了鸡血一般亢奋,爆发出马拉松运动员一般的顽强生命力。每天凌晨二点起床,攻坚外语。天随人愿,1996年,他终于以同等学力考取了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师从郁贤皓先生攻读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
在考博过程中,刘运好也闹了至今令人汗颜的笑话。当时,文兵老师告诉同等学力可以考博,整天卷缩在生活的小圈子中,哪里见过“同等学力”这个词呢?臆想“学力”这个词应该就是“学历”,于是在填表时,都写成“同等学历”,后来被他的师兄——当时在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处当处长的潘百齐先生,狠狠“涮”了一把:“同等学历的师弟来了。”最难堪的是,考取博士以后,他去拜访导师郁贤皓先生,请教读博期间相关读书的问题,谁知竟被老师狠狠地“骂”了一通:“马上就是博士生了,出手就写错别字,这怎么行!”他战战惶惶,大气也不敢出一声。他想,大约是他专业考试答卷太匆忙,试卷上有不少错别字吧。直至文学院举行老师和新生见面会时,他才恍然大悟。那天,他去文学院,一看开会时间还早,就去文学院资料室漫无目的地翻阅图书,突然看到我导师的著作《李白丛考》《唐刺史考》(修定本《唐刺史考全编》),那一刻真是“汗出如浆”了。原来,在考试结束后,他给导师写了一封信,详细说明了他之所以年龄这么大才考博的原因,希望通过“感情牌”打动他的导师。谁知画虎不成、弄巧成拙,竟然他把导师的名字“皓”写成了“浩”。在六安师范的图书馆里,哪里有这种专业书籍,所以报考前他对导师一无所知,他的借调在教育厅工作的同学在电话里告诉他报考学校、指导教师时,他也没有详细询问导师姓名的具体写法,结果犯了如此令人不可饶恕的错误。他的导师真是一位心胸如海的人,并没有因为他犯这样低级的错误而影响录取,他的专业课成绩、面试成绩都是第一名。对他来说,导师真是恩同再造呀!如果不是把他引上学术之路,刘运好可能至今还在学术的篱笆外流浪呢。
博士毕业后,在余恕诚老师建议下,刘运好回到了母校工作。第一次真正走向高校教师的行列,开始了新的生活,内里充满无限憧憬。开始,他一直认为“教书是主食,科研是零食”。但是,一件事改变了他的观念。1976年元月,方可畏老师将他对《文学批评与鉴赏论》的意见及“序”连同书稿一起寄给他。因为那时忙着考博,没有时间修改书稿。读博以后,因为没有读硕士,基础薄弱,读书写作,焚膏继晷,哪里还能顾得上书稿的修订。工作后,他一边上课,一边修改书稿,再次系统梳理中西关于文学鉴赏和批评的理论。于2002年由余恕诚老师推荐,在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2004又出版修订本,前后印刷了十余次,发行了数万本,这是他所有著作中发行量最多的一本著作。在此书的修改、修订过程中,他的理论修养获得了很大提升,也建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在古代文学作品选的教学过程中,以理论驾驭文献,由直觉上升理性,显然又提升了古代文学作品教学的理论和审美层次。此后,每写一部书,就感觉自己或在文献、或在理论、或在抽象思辨上有比较明显地提高。这时他才深深地感觉到“科研是基础,教学是致用”。作为一名合格的高校老师,教学与科研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2003年暑期,刘运好顺利评上教授后,他想现在必须做一个长久的学术规划了。因为没有经过硕士阶段的学术训练,他的读书杂而不成体系。博士阶段虽然相对集中于魏晋文学研究,但是魏晋时期的文学研究,有其特殊性。这一时期虽说已经进入“文学自觉”时期,但是文学的边界仍然比较模糊,应制、咏史诗之于史学,赠答、拟古诗之于经学,玄言、说理诗之于玄学,都有剪不断的丝丝缕缕的联系。所以,他在读博以及后来一段时间的研究也非常“杂”,有史学,有经学,也有别集。为了集中力量,重点突破,刘运好拟定两个基本规划:一是整理一部诗人别集;二是系统梳理魏晋经学与诗学的内在联系。2003年职称刚一解决之后,刘运好就申报了一个别集整理项目《陆士衡文集校注》,2007年出版之后,紧接着于2008年,他又申报了《陆士龙文集校注》,于2010年出版。做“二陆”文集前后用了七年时间。这七年时间,真是不分白天黑夜,除了教学,所有时间都用在文集校注上。七年来从未上床睡过一个囫囵觉。实在困了,就是沙发上蜷缩一会儿,每夜睡两三个小时,已成为一种生活常态。记得2007年初夏,《陆士衡文集校注》完稿那天,他一夜没有睡,将文稿打印完毕,已经是清晨五点左右了。晨曦初露,天光云影涌于窗前,他泡了一杯浓茶,一边抽烟一边喝茶,心里的滋润难以形容。现在看来,因为初次进行文集校注,水平、经验都十分有限,所以文集校注有些地方比较粗糙,不尽如人意处也在所难免,但是从题解、注释到版本、行迹考辨,确实下了一番苦功夫。十余年后,再次修订“二陆”文集校注时,还是很感叹当年所下的苦功夫。
由于预先对项目难度估计不足,结项又十分匆忙,许多问题的论述浮光掠影,甚至付之阙如,显然不能准确地反映魏晋经学与诗学复杂的内在逻辑关系,于是需要静下心来,开始重新审视原来的课题。刘运好计划分为三步走:第一步,深入研究全书的逻辑结构,从历史与逻辑、历时与共时、文化思潮与诗学生成的多维视角,重新设计全书的理论框架;第二步,依据重新设计的理论框架,再细致分类,提炼专题,各个突破;第三步,在各个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再回归于全书的理论框架,整合书稿,拾遗补缺,并提炼带有体系意义和方法论意义的理论范畴,为持续性研究指明方向。
思路明确之后,就开始按部就班地具体研究了。首先还是从魏晋经学做起。为了脱去经学史研究的桎梏,必须从重新钩沉经学文献开始。以历代史书及《二十五史补编》的经籍志、艺文志为抓手,以经学文献专书如《经义考》为补充,再分别考索史书中的人物传记,先做了一个详细的“魏晋经学著作一览表”,通过钩沉考辨,将见诸后代史籍的经学学者及著作直观地呈现出来,为推到泛滥学界的魏晋经学“中衰说”提供翔实的文献依据。然后选择魏晋经学中成就最大、官学影响最深的王肃,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再次深入文献,写出《王肃年谱》(没有收入《魏晋经学与诗学》)。通过爬梳剔理,魏晋经学的真实面貌已经呈现在眼前,再撰写魏晋经学通论性的文章就易如反掌了。仅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写就《从崛起到鼎盛:魏晋经学“中衰”论辨正》长篇论文,后来发表在《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上,也就是《魏晋经学与诗学》上编“概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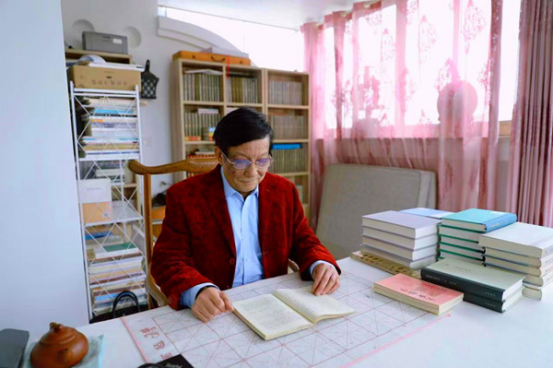
接下来,他进一步细致具体研究魏晋诗学,原来结项时只是收录此前零星发表的涉及儒学诗学和玄学诗学两个方面的论文,而经学诗学、佛教诗学则基本付之阙如。于是他首先从十三经所收录的四部经学著作入手,系统研究了王弼《周易注》、何晏《论语集解》、杜预《春秋左传注》、范宁《春秋谷梁传注》,补写了这四部经学著作特点的专题论文,因为何著和范著诗学内涵并不丰富,而王弼经学诗学既具有丰富的诗学意义,又暗含经学向玄学理论形态的转换,所以补写了王弼经学诗学两篇,杜预经学诗学一篇。另外,经学虽然以儒学为核心,但是二者又不相同。经学的本质是学术,其理论形态在于学理性;儒学的本质是致用,其理论形态在于价值论。因此,经学诗学与儒学诗学也有细微区别。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刘运好又特别研究了生成于佛学语境下的陆机诗学,以及《抱朴子》的文学功能及文章美学。关于玄学诗学在原来论嵇康“声无哀乐”之外,又撰写了陆云、郭象的本体论诗学、以及张湛《列子注》“至虚为宗”的美学意义等相关论文。魏晋佛教诗学论文虽然较多,也有“佛教美学史”研究之类的专著,但是现有研究有一点偏离,即将汉译佛教作为审视对象,偏离了“中国佛教美学”研究;有两点薄弱,从“中国佛教美学”的视角上说,理论范畴研究薄弱,理论体系研究薄弱。他的研究从第一个薄弱点切入,在原有论慧远“神趣”说的基础上,又细致研究了支遁“理中之谈”、僧肈“象外之谈”以及“文外之旨”从佛学到诗学的意义转换等。最后,以《华阳国志》所涉及诗学文献为个案,烛照其诗歌及诗学理论的生成。在这一研究过程中最大的收获是使他明确了魏晋以降,中国诗学的民族特色主要表现为“一体两翼”即以经学为主体、以玄释为两翼。为此我就撰写“魏晋诗学理论体系及其嬗变”,发表在《江海学刊》上,后又转载于人大复印资料,这就是魏晋诗学论的“概论”部分。
中国诗学“一体两翼”理论形态构成的发现,实际上也为未来进一步研究中国诗学提供了理论切入点。所以在论经学与诗学关系的“概论”中开宗明义提出“经学化诗学”的理论概论,并以此作为中国诗学的民族特点。当然,作为思想观念的经学影响诗学比作为审美观念的经学影响诗学,内在的因果逻辑更加复杂。这表现在:第一,在理论路径上,经学深刻影响学术变迁、士风嬗变,才可能对诗学产生深刻影响。第二,在理论形态上,魏晋以降,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是“一体两翼”的倒三角的鼎立关系。一方面玄释通过对作为本原的经学的摄取、容纳,形成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另一方面经学又在玄释的反哺、圆融中,其理论形态发生了微妙变化,二者生生互证,这种复杂的理论关系也使诗学的理论形态呈现出复杂多样性。第三,在诗学思想上,“六经皆文”固然是中国文学家根深蒂固的文学观念,即便如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仍然以“原道”“宗经”为作为理论支点,然而玄学的“性情自然”“言意之辩”及佛学的“般若性空”,又作为独立的理论形态渗透于诗学思想之中。第四,在诗学实践(诗歌创作)中,经学成为魏晋文学复古之风的源头,而玄学的勃兴,渗透于诗歌创作之中,使魏晋诗风呈现出不同的时段性;佛教的加持,又使东晋诗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如此细致地考察之后,自然抽象出作为本原的经学与诗性思维、审美范式及话语方式的内在联系,从而揭示出中国诗学与西方诗学迥不相同的民族特色。
在研究魏晋经学与诗学过程中,又发生了一个生活的插曲。2014年,爱人患乳腺癌,在北京住院,手术、化疗,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必须有人陪护,刘运好自然义不容辞。在北京陪护爱人生病期间,没有办法看书、写作,于是他趁着白天在给爱人药房拿药、看护吊水、料理生活的空隙,晚上爱人休息之后,抓紧整理已经写就的书稿。再次将从没有发表过的专题抽取出来,进一步发掘、抽象、加工、润色,给相关刊物投稿,这就形成了后来数年间发表论文的高潮。这本书的主体是由58篇论文构成,其中发表在包括《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献》等南大核心期刊(CSSCI)论文就有39篇。
其实,在医院陪护爱人时所修改的论文,不止于“魏晋经学与诗学”研究,还有“陆机陆云考论”。他在读本科时,就特别喜欢唐宋文学,后来又对古代文论着迷。
读大学时,刘运好一直想研究陆机《文赋》却无从下手。读博之后,因为选定的是汉魏六朝文学作为研究方向,陆机研究才真正进入视野。然而,并未专门用力,只写了一篇《“缘情绮靡”与陆机诗风》的文章,博士毕业那年发表在《宁波大学学报》上。在做“二陆”文集校注时,才特别用力。陆机文集校注出版之后,陈尚君先生发表一则短文,批评陆机集误收的两篇作品,刘明先生也发表文章批评他的《陆士衡文集校注》以及后来出版的杨明《陆机集校笺》使用底本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引起了刘运好的高度关注。所以后来,在做“二陆”文集校释时,他特别注意这两个方面:第一,一切电子版如《四部丛刊》《四库全书》所涉及的文字一律回归于纸质文献;第二,举凡校勘,必须亲自搜罗诸种善本,必须亲历亲见,切不可相信耳食之言。做陆云集校注时,有的版本藏于台湾省故宫博物院,他就亲去台湾查访善本,所有台湾省所藏的二陆集善本,他一一复印,装订成册。第二次修订二陆文集校注时,他抽换了原来所使用的底本,一一重新加以勘校;重新从诗话、文话、《文选汇评》、明清选本等纸质文献中搜罗、补充后代的集评文字;逐条补充原注的缺失、匡正原注的谬误;对原先所撰写的题解、段意概括以及考辨性文字,逐一删改、补充、润色。这是一种“脱胎换骨”式的修订,虽源于旧作,实际上已是新著了,所以更名为“校释”,以新著的形式重新出版,这就是收录于“江苏文库”中的二陆校释本。也是天赐良机,后来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又拟重新出版二陆文集校释的单行本,于是他就抓住这一机会,再次修订,这次修订主要是以校对引文、增删注释、润色文字为着眼点。其工作量虽然没有第二次修订那样繁重,但也不算轻松,因为修改文字大量都是在清样上完成,而且修改又需要以繁体正楷书写,几个月不停的劳作,胳膊肘处常常疼得难以动笔,但是他仍然咬着牙坚持了下来。书稿校对结束之后,他去医院检查,医生竟然说是“肘肌肉劳损”,很让其感慨:看来,燃烧的学术激情也仍然不敌岁月对生命机体的侵蚀啊。

后来对二陆文集校释的两次修订,刘运好还算满意,还得力于在“校注”与“校释”之间对二陆的深入研究。在做二陆校注之后,发现许多问题在“校注”时难以说清楚,于是他就打算写一部二陆研究的专著,一是将散落于“校注”中的生平著述、文集异议加以系统梳理;二是从历史、时代、主体上深入探寻二陆人生悲剧的发生原因;三是研究二陆思想的同异;四是分类研究二陆的文学创作;五是追溯二陆文学的文化生成;六是系统考查二陆的文学史影响。最后,更深入细致地考辨二陆年谱和作品系年。实际研究的次序与后来出版的《陆机陆云考论》次序并不相同。第一步,生平著述、文集异议研究;第二步,作品分类研究;第三步,综考历史外证和作品内证,研究思想、文学理论体系;第四步,研究二陆悲剧的成因。在这些研究已经成形并发表了相关系列论文之后,他于2015年申报了教育部后期资助。获批之后,他集中精力从历时和共时两个维度,立足于文化诗学,深入探讨文学生成和影响。在2014年陪护爱人过程中,所修改的论文也包括二陆的系列论文。《陆机陆云考论》(中华书局2020年)的主体也是由28篇论文组成,其中包括《文学遗产》在内南大核心期刊论文近20篇。
刘运好回顾自身所走过的学术之路,有三点深切感受:第一,学术研究要有明确的目标意识、深情的家国情怀以及历史责任感。宋代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子语录》)这是学术的意义,也是学术研究者的使命。第二,学术创新需要深厚的积累、丰富的阅历、深刻的思考以及驾驭语言的能力。刘勰说:“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文心雕龙·神思》)这是学术创新的基本规律。第三,学术动力源于超越功利的精神满足、追求真理的献身精神,唯有如此,才能如王羲之所说:“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兰亭集序》)
从生命规律上说,而今刘运好已是老境横生,但是按照现在的生命节奏,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未来的路仍然漫长,他仍然必须为祖国的文化建设添砖加瓦,必须为文化强国贡献绵薄之力,为建构中国学术研究的民族话语体系而孜孜追求!(素材来源:刘运好自传文章)
原文阅读链接:【中国网】http://t.m.china.com.cn/convert/c_0vbJyAi7.html
 最新更新
最新更新